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韦尼·萨德霍尔茨 Win.克特泽尔①
①贸易对腐败水平的影响可能通过我们提到的结构和文化两个渠道(两者之一或两者同时)发生作用。我们的数据不能确认哪一个效果更强一些,但是这可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提要:此文将腐败界定为公职人员为了私人利益滥用公共职权,并采用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指数来衡量不同国家的相对腐败水平。作者运用了多变量计量分析的方法,对50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作了比较研究,得出以下三条结论:(1)国家的个体经济自由度越大,则腐败程度越低,或者说,国家对经济控制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高;(2)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的民主价值越弱,则腐败程度越高;(3)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低。
腐败就像贫穷一样,可能会长期伴随我们。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很多国家都被重大腐败丑闻所困扰,包括法国、意大利、肯尼亚、墨西哥、韩国以及美国。腐败问题已经进入一些主要国际组织的议程,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腐败对任何政治体系都能导致问题,它还直接威胁一些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首先,腐败行为秘密进行并为一些团体(比如那些受贿者)提供特权,这就违背了民主制度中的开放和平等这些核心规范。其次,它也违背了现代政治机构的一般原则——公共事务不应以个人方式处理,而应采取公正的、基于规则的方式。最后,腐败现象会导致政治研究中一个常见的难题,即存在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文化之间的那种处处可见的鸿沟。尽管法律致力于消除实践中的腐败,文化却在不同程度上容忍腐败。
近年来有关腐败的政治学研究令人奇怪地匾乏,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性腐败丑闻不断发生的情况下。目前已有的研究很不完善。一方面,我们可以轻易列出很多国家和各个历史时期有关政治腐败和官僚腐败的详细说明,我们也可以援引一些专门问题的激烈争论,比如腐败是否有助于或阻碍经济发展,或者如何设计公共机构才能减少腐败行为;另一方面,文献却很少能回答大范围比较研究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腐败的程度是否随着国家的变化而变化?为什么变化?如果民主制度和腐败水平之间存在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
在这篇文章里,为了进行腐败的比较分析,我们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私利滥用公共职权。我们提出一套用国内经济结构、民主制度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解释腐败程度的假设。本研究利用最新的各个国家的腐败水平指标对以上假设进行了检验。
本论文的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已有的关于腐败的研究。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和一套派生假设。第三部分定义变量,解释指标体系,并给出数据。第四部分是数据分析。在结构中我们发掘了一些更深的含义。
一、我们所知道的
虽然近年来关于腐败的政治学研究不是很多,但前人的研究已留下了一个丰富的体系。那些研究大多着眼于解决一般腐败分析的核心问题。我们只简要讨论一下对目前研究有直接重要性的两个问题:比较数据问题和腐败的定义问题。
1.案例研究和数据问题
除了几个明显的例外,关于腐败的主要实证性研究是由单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构成的(正如Manzetti和Blake,1996年注意到的)。例如,Heidenheimer,Johnston和LeVine (1989)搜集了分析单个国家或地区的25个案例研究,他们的参考书目则列出了更多的案例研究。这些卷目包括三份讨论两到三个案例的论文,和一份分析了很多拉丁美洲总统的论文。其他卷目类似地提供了单个国家的例子(Markoyits and Silverstein,1988;Livi and Nelken,1996)。还有一些足有一本书容量的有关法国(Meny,1992)、加纳(Morris,1991)和墨西哥,以及更大地区诸如亚洲(Palmier,1985)或非洲(Williams,1987)的腐败现象的精彩论述。但是很少有研究既是比较性又是实证性的。Manzetti和Blake(1996)评价了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市场改革对腐败的影响。Gillespi和Okruhlik(1991)提出了一个研究腐败消除政策的分析框架,并提供了对中东和北非25个国家的一个分析。虽然Scott早在1972年就直面研究中的挑战并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解决方案(Scott,1972),但这种对腐败的比较性实证分析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腐败比较研究的一个巨大障碍是腐败活动可用数据的缺乏。Williams甚至还提出缺少有关腐败的“硬”数据现象可以解释美国的政治学家对该研究的相对忽视。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比较分析数据的问题:“因此,看起来,研究腐败的学生所使用的‘证据’不可避免是断断续续、偏颇、叙述性、潜在误导性。印象主义和不完全的”,因而不能支撑比较研究的一般理论(Williams,1987)。腐败现象的数值性数据的缺乏,其原因也不难想象:腐败行为秘密进行并通常一直保持秘而不宣状态:即使腐败的“受害者”也经常意识不到他们已经受害于其中;那些关于腐败的报道可能来自于意图低毁对方的政敌;对腐败现象的批评通常涉及赞扬或贬低特定团体;并且政府也可能不希望研究者涉足此类敏感领域(Noonan,1984;Williams,1987;Klitgaard,1987)。
由于缺少关于腐败的跨国数据,学者们一直不能对不同国家间腐败的相对程度发表多少意见,也不能用各个国家政治或经济的差别来解释腐败水平。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腐败研究中的这项空白。
2.定义腐败
实际上从60年代至今,发表的有关腐败的每项研究成果,都在斟酌如何定义腐败。既要表述清晰并能经受实证检验,又要求腐败的定义适用于不同文化。但残酷的事实在于,一个社会认为是腐败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个文化背景下被认为是无害的甚至是合适的。因此要给出通用的定义,就必须面对腐败的这个不可避免的特性。
在每一种定义下,腐败活动都是不适当的或是不合法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在于,要给出“不恰当”这个词的程度。但是研究者通过什么标准来判断某个特定的交易是否为腐败?政治学文献提供了三种主要的方法,分别基于公共利益。公众意见和法律规范(Scott,1972)。第一种方法是依靠政治或行政官员是否侵犯公共利益来判断其行为是否恰当(Friedrich,1996;Rogow and bosswell,1963)。就是说,公职人员通过牺牲公众利益来讨好某些特定集团,以获取私人回报。但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却有着不可救药的模糊性,由于没有方法可以确定一个客观的公共利益(Scott,1972;Throbald,1990),几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和某人对公共利益的定义背道而驰。
基于公众意见的方法认为,由于腐败标准的可变性,那么公众如何想,腐败就是何种样子(Gibbons,1989)。但是其相应的公众是指政治精英,是指政治动员的民众,还是全体民众呢(Scott,1972;Theobald,1990)?而且公共事务中何种行为是正当行为的观点,不仅在不同群体之间会有变化,而且在一个国家内也随着不同地区而变化,随着时间而变化。
基于法律规范的方法,则把腐败定义为那些违反“保证公共职责正常执行的特定规则”(Williams,1987),和那些以政治权益“非法交易”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Manzetti and Blake,1996;Heidenheimer,Hohnston and LeVine,1989;Williams,1987)。但是法律本身也可能是模糊的(Lowenstein,1989)。基于法律规范的方法也存在和其他两种方法同样的局限性:法律因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并经常易受有权势政客的操纵(Williams,1987)。基于法律的定义也可能会排除那些被广泛认为不正当,但可能并不是违法的行为(Moodie,1989;Theobald,1990)。
虽然对如何定义何种行为是不正当的和非法的缺乏一致意见,事实上关于腐败仍存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通用定义。这种定义的核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别(Theobald,1990;Palmier,1985;LeVine,1975)。Nye被广泛引用的定义就突出了公私之间的区分:腐败是“由于私人相关(个人、近亲、私人派系)的金钱或地位获益而偏离某个公共角色的正当职责的行为”(1989)。这样,腐败就破坏或模糊了公私问的区别。第二个要素认为腐败是一种交换,一个政党为某个公职人员提供诱惑(不一定是金钱)以换取特殊政策或行政优势,抑或“政治利益”(LeVine,1975;Manzetti and Blake,1996)。一些分析家已经将这个交换尺度当做“市场中心论”(Heidenheimer,Johnston and LeVine,1989;Van Klaveren,1989)或“政治经济学”(Rose-Ackerman,1978)方法的核心。第三个要素是对这种交换是不正当的感觉,就是说,他们违反了已有的规范。因此,腐败就是公职人员“偏离当前实际流行或被认为是流行的制度”(Friedrich,1989),或偏离了“公认的制度”(Huntington,1968)的行为;或者认为是一种“与政治制度背道而驰的政治行为”(Morris,1991)。有了这三个要素,我们就可以对腐败有一个可用的概括性定义:为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职权。
3.腐败的比较研究方法
很多关于腐败的研究,被如何在不同文化制度基础上给出一般性的腐败定义所困扰。也就是说,寻求观察或衡量腐败程度的研究者会很快发现:在一个社会里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现象,在另一个社会可能会被认为是恰当的。允许进行比较研究的惟一途径,就是预先指出该分析将采用哪种“不恰当”的定义。这样,研究就要采用一套由特定的社会群体定义为“腐败”的行为,并对这些行为在不同国家的发生情况进行比较评价。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就采用了这种研究策略。因此,我们就不用伪称是根据每个社会自己的条款术语来衡量腐败了。相反地,我们使用某个群体的观点作为一个标准。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科学策略;该研究中的“腐败”是一个分析范畴,它的作用在于可以进行比较分析。
更早受腐败比较分析困扰的研究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比如Bayley(1989),就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广泛认同的西方标准来评判贿赂、裙带关系和滥用职权等特定行为。否则,那些“选择与文化相关的定义”的西方研究者,“要么遗弃这个字眼结束研究,要么就不得不针对每个要研究的非西方国家而重新对该词进行特别的、可能不同于前者的定义”(Bayley,1989)。如果认识到社会背景的复杂多样性,分析者也可以注意到一些出于研究目的被归入腐败的行为,在某些社会其实并不会引起社会或法律的谴责。Nye意识到这种“用西方标准把特定行为一般性地归为腐败行为(包括贿赂、裙带关系和滥用职权)”的方法,具有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优点(1989)。
非西方国家使用西方关于腐败行为的标准时,系统的偏差可能是很小的。正如Bayley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社会服务较高等级,都“熟知西方所标注的‘腐败’,并能将其应用于他们自己的国家”(1989)。Nye也同样写道,西方标准“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至少是部分相关的”(1989;also Klitgaard,1987)。Scott则论述道:“由于非发达国家中公共行为的法律标准和西方国家十分相似——源自于殖民传统,这样,比较研究的术语规则就大体相似了。”(1972)的确,在非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斗争研究中,那些旨在消除的行为正是那些西方标准制度描述的行为。
总的来说,为了实证分析,本研究中的“腐败”指的是被西方标准认为是不恰当的行为。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特定的几种行政腐败,而不包括竞选活动等。我们有关腐败的数据包括国际商务人员和咨询人员对不同国家中他们认为是腐败事件的评价。该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是跨国业务和咨询精英们所感觉到的国际商业活动中的行政腐败水平。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会更完整地描述这些数据的来源。
二、预测腐败
我们在解释腐败行为程度时主要采用两个尺度。第一个是机会和激励结构。该尺度着眼于某个给定政体下人们面临的潜在的动机模式。虽然很多分析家都认识到了机会和激励结构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传统领域的学者最关心的还是法律和官僚体系为不同角色的职位设置的激励和惩罚机制(Rose-Ackerman,1978;Klitgaard,1987)。
第二个尺度是文化,可以理解为“由经验到行动的有关认知、情感以及评价方案的指令系统”。这些指令构成了“行为导向”:“在一些情况下以某些方式行动的大体安排。”行动者可以通过一个“文化社会化”的过程熟悉这些导向(Eckstein,1988)。很多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腐败问题中的结构尺度和规范尺度,而不一定要明确他们之间的作用(Rose-Ackerman,1978;Morris,1991;Manzetti andBlake,1996)。
这两个尺度在分析性上是彼此独立的。这就意味着,两个国家里的两个官僚主义者可能会面临相似的法律一官僚机会。比如说,像申请某些种类的商业执照者,在低工薪、对执照审批的单独控制以及松懈的监督等情况下勒索回扣这种事情,如果被社会化的文化对行为提供了不同导向的话,他们的行为就会迎异:在一种文化中,行政勒索可能是可以预料到的,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则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同样,同一种文化下的两个行政管理人员如果被置于不同的官僚体系中,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行为来。或者,换一种角度,就算在那种看来机会有利于腐败行为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当前盛行的文化导向仍然可以阻挡人们利用这些腐败的机会。而在文化导向允许腐败行为的地方,正式法律和组织又可能会阻碍这些行为。
下一步是把政治一经济结构和腐败之间,以及文化和腐败之间的关系理论化。为了作出关于政治一经济结构的假设,我们着重注意个体经济自由(与国家控制经济相反)的程度。当国家及其管理部门对经济实施相对较高程度的控制时,公职人员就有权决定谁将接触经济资源和经济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的成功可能更多地依靠影响官员的能力,而较少凭借市场活动。这样的话,贿赂、勒索和回扣将变成影响财富分配的有效途径。就像Scott所说的,“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和管辖范围越大,某种行为可能符合我们的腐败标准的概率就越大”(Scott,1972;Tanzi,1994)。相反地,当经济产出大部分来自于私人决策(在国家控制之外)时,国家就可能不被当作经济资源的关键配置者了。私人经济活动看起来比政治/官僚影响更能促进经济繁荣。这样来说,高程度的个体经济自由性意味着减少对经济机会的政治控制,也意味着更少参与腐败的激励。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一:个体经济自由度的大小应和腐败程度成反比。或者说,由于个体经济自由度是国家控制的反面,则国家对经济控制的程度应和腐败程度成正比。
第二套假设是关于文化和腐败间的关系。政治文化包含了各种情形和行为导向之间的联系。腐败的文化尺度和结构尺度同等重要。Rose-Ackerman(1978)撰写了政治经济研究方法最初的综合陈述,论述了结构和文化(价值)对腐败行为都十分重要。她的书重点放在“结构性动机”上,认识到一种“研究政治的经济方法……不能解释要保护一种混合经济所应具备的民主及个人理想的起源和转变”(Rose-Ackerman,1978)。事实上,她明确指出“如果一个人想理解民主的功能,如果像传统经济学家那样忽视自我寻求行为上(Self-Seeking Behavior)的道德约束,则不可能如愿”,并且某些类型的“政治价值”和“道德信仰”对于公众和政客都是必要的(Rose-Ackerman,1978)。Della Porta和Rzzorno发现了“腐败程度的变化程度,更多地依赖于人们愿意腐败变化程度,因此也就更多地依赖于我们如何命名参与腐败所付出的道德代价,而不是依靠机会的结构”(1996)。我们可以通过讨论民主制度和价值对消除腐败行为的特殊作用来寻求这样的建议。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腐败的定义涉及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个现代概念,出现在18世纪,并一直传播到19甚至20世纪。从前的陈述,则认为这是皇室家族权力的一种延续,公共职务是君主的个人财产,可以按照他的意愿随意分配(或出卖)(Scott,1972)。逐渐地,统治的权力不再通过国王个人的继承,而是来自于人民的意愿(Bendix,1978)。后来,理性的合法的官僚制度(采用Weber的术语)代替了世袭行政。现代官僚制度,正如现代政治权力一样,要求“职责和职位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区分(Theobald,1990)。民主制度体现了这些理想。在一个民主制度里,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取决于他们的合法性,大体上取决于民众(或大部分民众)的意愿。因此,公共职位就成了一种代表人民而执行的委托信任,而不是为了在职者的个人利益。腐败违反了民主制度的两个核心规范:平等(腐败意味着特殊通道和影响)和开放(Della Porta and Pizorno,1996)。
我们相信,民主制度和价值(文化取向)对于给定的机会结构都能产生较低程度的腐败。一个政治文化越强调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并以对群众意愿的职责定义公共职务,就会有更多的人民认为腐败行为是不恰当和不合法的。更进一步地,我们希望发现一种社会化的效果(Eckstein,1988)。一个国家经历民主制度越久,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就越能根植于社会。基于这些考虑,我们给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二:民主制度和价值的强度与腐败程度成反比。
最后,我们预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会通过贸易和投资对某个国家的商业和行政管理产生影响。较多地参与贸易,既能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在结构方面,更自由的贸易将从官员们的手中夺去一些可以换取私人收益(贿赂、回扣)的行政权力(执照、许可证。减免证等等)。文化观点与社会化有关。国际商业和金融受到来自OECD国家的公司的统治。这些法人代表可能会采用基于“西方”规范的一套跨国商业文化(LeVine,1989)。这种跨国商业文化,既包括一些相对比较表面的习惯(穿着何种衣服,如何取悦来访者),同时也包括西方盛行的商业运作标准。这些规范禁止一系列广泛范围的腐败行为——贿赂、勒索、裙带关系和回扣。随着一个国家的商务人员和官员与国际经济联系的增多,他们应投身于跨国商业文化中,并提倡对腐败进行更严格的禁止,从而形成一套跨国反腐败制度。比如,Maclean(1973)论述道,由于法国于80年代向世界经济开放,法国的商业文化就要去适应跨国商业规范,包括更大的透明度,这部分地解释了80年代和90年代频发的商业政治丑闻的原因。因此我们的最后一个假设是:
假设三: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应和腐败程度成反比。①
①这个指数综合了十次不同的民意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国家进行。其中三个调查分别来自于1993年、1994年和1995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咨询了最高执行官实践中的不恰当行为(例如贿赂)。三个调查来自于1993年、1994年和1995年进行的“政治经济风险咨询”(Hong Kong),这项调查测验了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管理者对11个亚洲国家的腐败水平的看法。其他调查由Impulse来承担,通过咨询大使馆和商会调查了103个国家的腐败水平。由于透明指数中的一个国家必须要包含至少四次调查,因此只给出了54个国家的腐败评分。
三、数据
正如上文所述,缺少腐败的通用标准以及缺少有关腐败行为的跨国数据已经成为对腐败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障碍。因此,这一研究中所用变量,并不是研究腐败的一个客观方法,而是基于那些跨国活动的精英们(任职于跨国企业、机构和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的感受。被用来解释变量的数据,是来源于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指数,该组织1996年对54个国家的腐败水平进行了评分。该指数实质上是一个“多个民意测验的综合”,综合了十次不同调查结果,这些调查的形式是询问跨国企业机构的管理和咨询人员在各个国家的经验。①用该指数来度量腐败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可以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并且这个指数采用了上文我们得出的腐败定义(滥用公共职权获取个人收益)。
①本文摘自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第6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
为了衡量政治经济结构,我们需要度量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程度。我们采用了“经济自由组织的自由指数”(Messick,1996)。该指标包括六个与个人经济权利有关的主要因素:持有财产自由、谋生自由、创业自由、投资自由、国际贸易自由以及参与市场的经济自由。1996年的经济自由组织提供了82个国家的数据,包括上文提到的我们已给出腐败评分的54个国家中的50个。由于经济自由指数可以直接评价个人公开参与,并从一系列市场活动中获利的程度,因此它对我们的研究十分有用。
为了获得政治文化对腐败的影响,我们采用两个表明民主制度在某个给定社会里根深蒂固程度的指标,一个指标衡量民主制度的广泛程度,另一个度量民主制度的社会化深度。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的自由指数代表了每个国家的民主范围(Karatnycky,1997)。政治权力包括:对拥有真正决策权的政治领导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组建政党的权利,不被军队或其他寡头集团统治的自由,真正的政治反对派的存在,以及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公民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结合1995-1996年的这些指数,我们可以衡量192个国家(包括上文中已给出腐败评分的54个国家中的53个)民主制度的广泛性。
度量对民主制度支持的深度的一种方法是看一个国家的民主政府已经存在多长时间。我们采用民主年限这个变量,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拥有民主制度的年数(Lijphart,1984)。政治文化通过社会化进程传播。因此,民主制度和价值在一个国家引导政治时间越长,这些制度和价值就越根深蒂固。
最后,我们采用贸易指标来衡量一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指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数据取自于世界银行1995年的世界指标(世界银行,1995)。
四、数据分析
为了开始分析不同国家腐败的影响因素,我们首先检查一下感觉的腐败水平跨国分布情况。国际透明组织的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指数,列出了从最不腐败到最腐败的国家。粗看表中的排名大体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几乎无一例外地,那些被认为是最不腐败的国家都是民主制的,有着较高的政治经济自由度的,并高度融入国际经济的国家。这类国家中排在表中最前面的几个包括新西兰、丹麦、瑞典、芬兰和加拿大。相反地,被认为是最腐败的国家是那些传统的集权制国家,在政治经济领域都几乎不允许个人创业,也较少加入世界经济活动。跨国商业精英感觉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肯尼亚,以及孟加拉国。
虽然大体上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那些做生意的人都认为新加坡是个腐败水平很低的国家,要比澳大利亚、荷兰以及美国的腐败水平都低,但是新加坡的居民并没有那些感觉更腐败的国家的居民那么多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度。另一方面,印度,这个已经有50年民主统治历史的国家,却被认为是非常腐败的,实际上按照这个样本所列出的国家中,只有8个别的国家比印度更腐败。最后,在该腐败指数中位于中间部分的有一些具有混合性质的国家和地区:有较高国际经济一体化水平和较少政治经济自由度(比如南非。韩国),以及有着较长民主制度历史(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些国家。这样一来,虽然表格在大体上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得出关于国家间腐败水平的普适性结论。
现在转向对假设更细致的检验。表1给出了单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感觉到的腐败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很好地验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每个解释变量的系数都在我们预期的方向上,并且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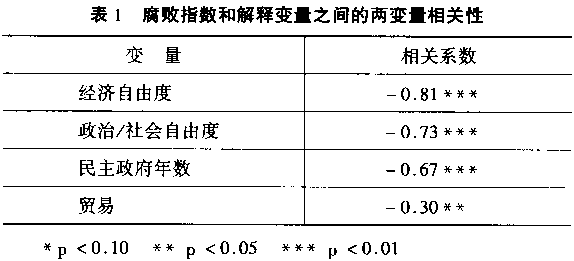
表中的数值代表腐败指数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由于数据的缺失,每个解释变量所用国家和地区的数目不尽相同。对于经济自由度,乌干达、厄瓜多尔、喀麦隆和香港没有包括在内;对于政治/社会自由度,没有包括香港。腐败指数来源:国际透明组织,1996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来源:Messick,1996年;政治/社会自由度数据来源:Karatnycky,1997年;民主政府年数数据来源:Banks,etal,1997;贸易数据来源:世界银行,1995年;所有国家、地区的数据来源:联合国,1995年。
我们的结果显示了:
(1)随着经济自由度的增长,腐败水平降低(r=-0.81,在<0.01水平上显著);
(2)随着政治民主自由度的增长,腐败水平降低(r=-0.73,在<0.01水平上显著);
(3)随着民主政府年数的增多,腐败水平降低(r=-0.67,在<0.01水平上显著);
(4)随着加入国际贸易程度的提高,腐败水平降低(r=-0.30,在<0.05水平上显著)。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控制经济的程度,对腐败水平的影响显著。政治经济结构越是鼓励“拿到桌面上”的行为,诉诸腐败的可能性越小。民主制度的强度也影响着腐败水平。有着广泛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国家比那些民主制度较弱或不存在民主制度的国家更少存在腐败行为。同样,一个国家经历民主统治的时间越长,民主价值就扎根民众越深,腐败行为也就越难于产生或越不被容纳。最后,正如我们所预计的,更多地加入国际贸易也与更低水平的腐败相联系。
接下来,我们作多变量回归来检验这些变量对腐败的解释效果。首先要确信这些变量在单相关性中是重要的解释指标,其次在包含其他变量时看这些变量是否在统计上显著,然后的问题是这些变量一起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腐败水平。表2报告了多变量回归分析,即用四个解释变量预测腐败水平的结果。
结果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预期。所有的变量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这个相对简单的模型解释了我们样本国家腐败水平将近80%。标准斜率系数检验显示每个变量都显著影响腐败水平。我们的模型中最有解释力的变量是经济自由度(B=-0.374)和民主政府年数(B=-0.330)。更高的经济自由度意味着个人可以在市场中通过自主选择达到经济目标,减少对运用腐败手段的需求。民主统治的年数表征文化尺度,一个国家获得更多的民主统治经验,公民逐渐将民主制度社会化,能形成指责腐败的社会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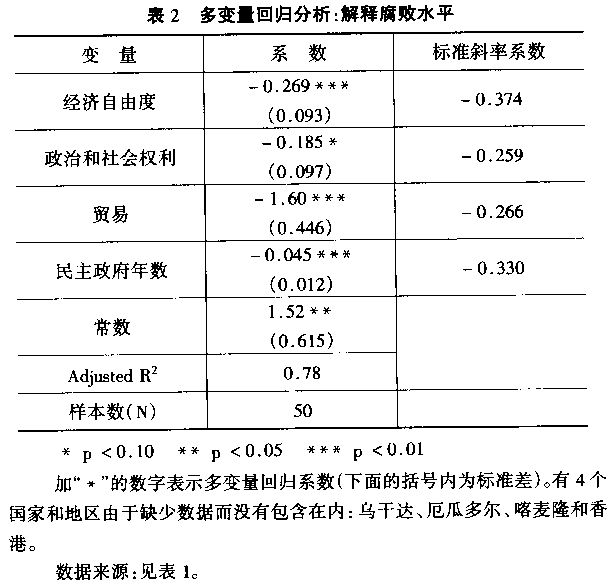
------------------
亦凡图书馆扫校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